陶潜与安妮之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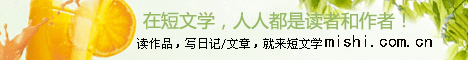
谈起隐逸,千百年来,总是离不开谈陶渊明。
陶浅的一生,经历了从富贵到潦倒的骤然转变。当然,这种处境的变化与其自身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就像一句话,心态决定一切。淡然跳脱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只能有最恬淡无争的生活方式,以最质朴单纯的状态存在于世。
以前读来,觉得他的诗句平淡,寡淡无味。执拗的以为他申明远播完全来源于现代人由于内心纯真缺失后的追捧。我从来没有以为他会真的有如此高深的思想境界。在我的观念里,物质就是物质,意识就是意识,这只是两种无法同一调和的敌对。况且我从来都是现实主义者,物质决定存在。也许当时太年轻。反复将这字字句句读来诵往,没有觉察丝毫的玄妙。
当然***如同墙上日渐剥落的粉白,显出原色。我认同这个人的隐逸,接纳让的安淡。最欣赏的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看似平淡的语句,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誓。细细品来,却有种玄机在里面,完好的契合了玄学的“回隐在心志而不在于形迹”。让我想起了一个作家--------安妮宝贝。喜欢这个看似颓唐的女子,颓废却不使人尽看的文字让人镇静和清醒。因此我想将她的小说与陶潜的诗结合来谈隐逸。尽管我不知道用这种非主流的文化形式往解说中国的主流正统文化,是否是对主流文化的亵渎。
安妮的长篇《春宴》出版了。大致讲得是一个叫周庆长和一个叫沈信得的女子各自的人生历程和状态。同样是来自于小城镇的女孩子,同样选择了上海这个繁华而纷杂的城市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不一样的心性,注定着一段不同人生历程的状态。
庆长淡泊萧然,对俗世保持着本能的敏感和警戒。在她的心里,始终筑着一道墙,防守和排斥内心所抵触的一切。尽管身处大城市,却完全没有沾惹上大城市的物质习气。在报社工作,常年采访,摄影,将工作的历程变成旅程,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旅程。喜欢深进地势偏远的地区,天高地远,与世隔尽。躲避外界强势汹涌的经济、政治、物化浪潮,带给人无以言说的安定,对那些真实的挖掘才是她工作气力的源泉所在。她喜欢上那些少数民族女子的发式和衣物,延续着传统的审美,有着无比的镇静与古朴。
她漠视认同,也漠视不认同。她只是她自己。难道这与“心远地自偏”没有融洽与吻合?周庆长身上的这一点,和陶渊明的恬淡无争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而她的生活状态,不似别的城市女子一般纷繁而复杂。耶稣头,自然的黑发,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不抹香水,喜欢穿手工制作的绣花鞋,穿球鞋,中性风格。看上起,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尽管如此,并不影响她个人魅力的散发。有清池这般优秀卓尽的男子真挚的从内质往爱上她,尽管终极他们是失败的,但曾彼此交付了真心。凡世纷杂,形形色色鲜明靓丽的女子与他擦身而过,独独倾心了不饰雕琢的她,那是一种深沉的爱,爱上的是她的心性。这一分高贵的孤独与固执的隐逸仿佛是她与生俱来的属性,凡人无法相比。
当她与定山这个有着可观财富,事业成功的中年景熟男子结婚,完全可以让自己鲜明。但婚礼上的她,没有穿婚纱,穿得只是一天白色的连衣裙,一双手工制作的绣花鞋。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看似***的行为只是她内心意识的果断。她每时每刻都在与世俗相接触,没有刻意的抵触,却自然的形成了对比。心性使她阔别他们。阔别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阔别熙攘而隔尽的人群,阔别形式感和物质堆积的生活,阔别妄想。生活本该是简单的,何必执着又复杂。她说,我们终极面对的,是一个庸俗的难以被轻易改造的世界。所以她保存了自己,这个世界独特真实的自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撼动。
我想,如此看来,周庆长的淡然颇似陶潜。
而信得好强倔强。在年轻的意识里,始终相信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业、名誉、能力、工作、人脉,这些都凭着她自身顽强的拼搏,从无到有。但物质的追逐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人疲累。当人疲累的时候,便不再相信物质,觉得它变成了羁绊,而始作俑者无非是内心强烈的欲看。我们总是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约定俗称的审美,规范,到最后失却了自身的棱角,到最后难以找到自我。
但信得是幸运的。屡次的尝试,探求,追寻,发觉了这疲累与纠结背后的真正原因,她能够抽身出来。与庆长一起往偏远的地区采访,支教。那似乎已经到达了大隐隐于朝的境界,由于她不是单纯的隔离与排除,而是经历挣扎后的涅槃。就像一个生过天花的人,挺过来就不会再生此病。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隐逸,经历了磨练的心智,有着不可摧毁的顽强。
而小说有写到她的脖子上刻下的刺青是一个“凛”字,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锋利清敏,仿佛是对世俗的挑战与宣判,这就是安妮赋予她的含义。凛然,固执,敏感,凛字与隐逸的心性不谋而合。
安妮小说貌似荒诞的情节和执拗的人物性格实则是她对于人生的清醒的洞察。一个人与所置身的时代,可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她始终在想这个题目,但是没有答案。一个试图与时代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人,始终要付出代价。
还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美和郑重被定义为矫情造作,恶劣习陋却能够引起群体的兴奋。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确实,事实就是这样,那些内心隐逸,没有妄想与过分欲求的人被看成这个时代的异类。他们本来不希奇,他们很真实。只是由于没有附和这个时代丑恶的褪变习气,就被排斥和嘲笑。这是时代的悲哀!真正可爱可怜的人是那些同流合污,趋炎附势的人!
依稀记得她的另一本小说《莲花》里面的墨脱,在历经了一段艰险曲折的道路,他们终于到达那个圣地。我在网上看过关于墨脱的图片,景色安宁而静谧,美好而恬远,美得似乎是哲蚌寺的壁画,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古朴中带着神秘。
那个叫墨脱的地方也昭示我们,人与所置身的环境之间,应该本能的保持一种疏离与惊醒,这样才能保全自我,真实的自我。而那份淡泊与隐逸的心志,是一种以意识的状态,并非物质或形式的存在。这就阐释了那句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假如,黑暗不能遮蔽使你不见,黑暗如同白昼般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一样。这是怎样的一种隐?



